李白与佛教
——兼论李白与九华山及金地藏
作者:何家荣
一
李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主导思想到底倾向于什么方面?学术界至今未能取得一致的认识。
著名的李白研究专家郁贤皓先生在《论李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指出:
有的认为“李白的主导思想还是任侠”;有的认为“李白的思想是充满许多矛盾的,而其中主要的矛盾,便是入世与出世,从政与还山,兼济与独善的矛盾”;有的认为“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代表”;有的认为李白主导思想是“法家思想”,是个“尊法非儒的人物”;有的认为李白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有的认为李白“是一个道教徒,在接受各种思想的影响中,受道教思想的影响最多”,“求仙学道是他追求的一个生活目的”,如此等等,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①
郁贤皓先生自己则认为:
李白一生的思想确实是复杂的,但这些思想并不是并列和始终不变的,而是有主次之分,并且随着环境和经历的变化而起伏的。……贯串李白一生的主导思想,无疑是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要求建功立业,为社稷、为苍生做一番事业,然后功成身退。这是李白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任侠、游说诸侯、隐居访道等等,实质上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都是为了达到理想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是为实现这一理想服务的。②
我们基本赞同郁贤皓先生的观点,但又稍稍有一点不同。综观李白诗文,似乎并不能梳理出一个始终如一的思想倾向。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李白不是一个以思想见长的人,他一生似乎没有一种明确的、坚定的思想(或理想);李白是一个精神之子,而且他的精神是自由而飘逸的,变动不居的。
任侠,似乎是李白与生俱来的一种禀性。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刘全白在《李君碣记》中说他“少任侠,不事产业”;范传正在《李公新墓碑》中说他“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李白自己在诗文中也写道:“十五观奇书”(《赠张相镐二首》),“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这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一定会终生流淌在血液里,只可能有时潜伏,而不会完全消失的。
求仙学道,追随道流,是养育他的故乡,也是整个唐王朝风气熏陶的结果。李白的仙道之好,也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写有《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诗。后来,大约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李白“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须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所以,他像所有士子一样,离开了家乡,到外面的世界追求功名事业。临行前,他写下《别匡山》一诗,表明心迹:“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要追求功名事业,就必须改从儒道,这对李白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但为了像一个大丈夫一样处身立命,就不得不改变自己,改造自己。
这种改变和改造,如果是一帆风顺的,就会鼓舞人满怀信心,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所谓顺势而为也。但是,事与愿违,李白的从儒之路却是异常的坎坷。这一点,从李白的大量诗作中可以明确看出来。如: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
《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献纳少成事,归休辞建章。十年罢西笑,揽镜如秋霜。”
《赠张相镐二首》(其一):“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其事竟不就,哀哉难再陈。”
此外,还有如:“无风难破浪,失计长江边。”(《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才将圣不偶,命与时俱背。”(《赠从弟宣州长史昭》)“空名束壮士,薄俗弃高贤。”(《留别广陵诸公》)“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五)“叹我万里游,飘摇三十春。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门有车马客行》)等等。
总之,李白在儒道上似乎始终看不到希望。正如他在《行路难二首》其二中写道:“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在李白的前方,儒道,犹如他故乡的蜀道一般,难于上青天。(按:梁、陈间诗人阴铿《蜀道难》写道:“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中晚唐诗人姚合《送李余及第归蜀》写道:“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子今称意行,蜀道安觉危?”)
面对儒道上的挫折与艰难,李白难免会产生怀疑和犹豫,“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有时甚至会觉得,自己涉足儒道,也许就是一个错误,“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野情转萧散,世道有翻复。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寻阳紫极宫感秋作》)所以,李白始终都在儒道和仙道(隐逸)之间徘徊,那匹精神的白鹿,实际上就是李白的化身,从来都与李白形影不离。李白还是骑着那匹精神的白鹿,在名山大川之间作他的酒仙、诗仙、神仙,更符合他的天性。
到了晚年,在仙道、儒道之外,李白又发现了一样美好的东西,那就是佛道。
二
李白的作品中,有关于儒教的很多,有关于道教的更多,有关于佛教的也有几十篇。
李白或许天性是倾心于仙道的(他正经入了道门,受了道箓),他自由不羁的精神也许正好与道家一门相通相契,“我本楚狂人”,可谓一语中的。
李白不是正统的儒者,他崇奉的不过是鲁仲连一类的高妙之士、游侠、儒侠,追求的是“道可济物,志栖无垠。”(《送黄钟之鄱阳谒张使君序》)③同样,李白也不是正宗的佛教徒。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在《李白研究——抒情的结构》一书中专列一章《李白的思考形态》,其中指出,李白以道教的游仙、求仙世界作为题材的作品在数量上比以儒家为题材的诗作多好几倍。他对儒道两教都存在着强烈的共鸣,同时对两教的各种状态都发表了一定的批判。在两教相互关系上,明确主张儒教先行,然后是道教的隐逸。李白吟咏佛教题材的作品数量相当多,但一般都有漠然的感觉。……李白诗中往往把道教作为主题作品,而佛教题材则大部分只是作为素材来使用。松浦认为,儒、道两教具有同质的对立性,所以可以相辅相成,而佛教则具有一种异质气氛,李白诗中的佛只是作为素材用了大量佛教用语,在主题上几乎都是道教式的隐逸。他对佛教从未提出过批判和怀疑,这正好证明他对佛教并不寄以深切的关心。④
《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这首诗最能说明松浦友久的上述观点。诗中“谪仙人”非佛家语,“酒肆藏名”非佛家行,“金粟如来”可谓恰如其分。
金粟如来,是佛教经典《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摩诘经》)中的主角,化身为居士维摩诘。《维摩诘经》中这样写道:
“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随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已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唐代文人,不只是李白,王维更为典型,他们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到诗歌表达形式,都表现出对《维摩诘经》的推崇和接受。张海沙在《唐代文人与〈维摩诘经〉》一文中指出:
“唐代文人及后世的文人普遍推崇《维摩诘经》,是因为推崇维摩诘这样一位优游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人物。这是中国传统中所不曾有过的、消解了人格上矛盾的人物。被推崇为圣人的孔夫子及真人庄子,其思想体系及日常生活实践都充满着未能解决的矛盾。同时接受儒道两家思想的传统文人更艰难地在入世与出世、济人与自适、个体与群体、有限与无限、精神与物质等矛盾中挣扎。维摩诘的观念与实践是如此地和谐,他以毕竟空观和不可思议解脱解决了困惑无数文人的矛盾。他将对最高真理的追求与平常生活融合、将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外在世界融合。”⑤
李白自认为是谪仙人(先是贺知章等人称许的,后来李白就当真了),维摩诘是转世的金粟如来,是人间佛。通过前引《维摩诘经》中加着重号部分,我们可以看出,这二人的身世、际遇确实很相似。所以,善于联想的李白,自然会想到,自己也像维摩诘一样,是金粟如来的后身。
但说归说,李白并没有真的像维摩诘那样,“奉持沙门清净律行”,“常修梵行”。李白到过一些寺庙,但都没有久留;他结识过一些僧人,但都没有深交。而且,李白与佛教(准确地讲是与僧人)相遇是比较晚的,估计是在他落魄江湖之后,前路渺茫之时。这一点,从他的一些诗作中大致可以看出来。如《僧伽歌》:“嗟余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秋日登扬州西灵塔》:“玉毫如可见,于此照迷方。”玉毫,即佛光。《法华经》云:“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迦吒天。”
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一首诗,即《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为了阐述的方便,兹引录如下:
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灭除昏疑尽,领略入精要。澄虑观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幸逢禅居人,酌玉坐相召。彼我俱若丧,云山岂殊调。清风生虚空,明月见谈笑。怡然青莲宫,永愿恣游眺。
诗中出现了大量佛教语,如“梦中”、“风火”、“假合”、“寂照”、“前后际”等。清人王琦注云:“释家以此身为地水风火四大假合而成,坚者是地,润者是水,暖者是火,动者是风。《楞严经》: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却求观世间,犹如梦中事。湛然常定之谓寂,莹然不昧之谓照。寂其体也,照其用也。体用不离,寂照双运,即是定慧交修止观互用之妙谛。《维摩诘所说经》:法无有人前后际断。……金仙谓佛。”
由此可知,李白与元丹丘所谈之“玄”,并非道家之“玄而又玄”,而是佛法。但其中兼有道家的色彩。李白好像是在向元丹丘谈起,他曾遇到某位高僧向他宣扬佛法,让他朗然了悟的情景。而非常有意思的是,两位道门弟子却在佛家的寺院里大谈佛法。我们可以说,在李白的意识里,佛、道没有分明的界线,佛和道并行不悖,妙合无遗。
李白自号为青莲居士,而莲花与佛、道两家都有密切的关联。《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九“西上莲花山”:“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这是道家的莲花。《僧伽歌》:“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亭》:“子见水中月,青莲出尘埃。”这是佛家的莲花。李白自号,也许兼有对佛、道两家的向往之意吧。
儒家、道家,李白都身体力行了;佛家一途,李白则只是神往,而没有力行。可以说,对于佛教,李白是不期而遇。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世界的香云、花雨,以及佛的智慧、僧人的闲适、寺院的幽远等,令李白深感兴趣,李白得以在那个世界里暂时安妥他落魄的心灵、迷惘的精神。
三
李白晚年流连于宣城、秋浦等地,于是,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李白与九华山的僧佛有没有关系呢?
李白于宣城、当涂、南陵、秋浦等地,均有与僧佛有关的诗作。《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七:“桃波一步地,了了语声闻。闇与山僧别,低头礼白云。”可以确定是写于秋浦,与九华山僧佛无关;其它诗作中也都有确定的地点。只有《寻山僧不遇作》一首,是写到什么山上寻哪位僧人,是否上九华山寻九华山僧,无从查考。
李白不仅没有有关于九华山僧佛的诗作,而且他有没有上过九华山,从他本人的诗文中也找不到依据。
李白写九华山的诗有两首,一首是《望九华山赠青阳韦仲堪》,诗题就很明确,是望九华山,而没有登九华山。另一首《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是与人合作的,诗前有序,序文曰:“青阳县南有九子山,山高数千丈,上有九峰如莲华。按图徵名,无所依据。太史公南游,略而不书,事绝古老之口,复阙名贤之纪。虽灵仙往复,而赋咏罕闻。予乃削其旧号,加以九华之目。时访道江汉,憩于夏侯迴之堂,开簷岸帻,坐眺松雪,因与二三子联句,传之将来。”从序文中可读出两点:一是没有登山的迹象;二是没有僧佛的迹象,“灵仙”、“访道”字样,到有一些仙道色彩。
但是,宋及宋以后诸人笔下,出现了不少有关九华山李白书堂的记载。如:王十朋《望九华》其六云:“九华山下化城寺,太白书堂高出开。”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写道:九华山龙女泉旁,“乃李太白书堂基,今为张氏坟地。”陈岩《李白书堂》(题下原注:化城龙女泉侧)亦云:“兰芷春风满地香,谪仙曾卧白云乡。山间精爽今犹在,落月时时见屋梁。”等等,皆言之凿凿,似乎不容人置疑。
宋人吴梦祈还写了《李翰林九华书堂记》,记中写道:“初翰林之弃官也,即有蓬丘之思,访道江汉,遥望九华峰,顾而乐之。会故人韦仲堪宰是邑,乃卜居焉。始易其旧号,加以九华之目。其居介乎龙女泉之侧,南渡之后夷为张氏之丘。”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李白途径九华山,是为了访道,李白在九华山(如果是真的),只是“卜居”,都没有礼佛的意思。另外,我们从李白与秋浦有关的作品中,也能看出,李白在这一带的主要动机是炼丹,是寻仙学道。如:
《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吾营紫河车,千载落风尘。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时登大楼山,举首望仙真。”
《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尝采姹女于江华,收河车于清溪,与天水权昭夷服勤炉火之业久矣。”
《宿虾湖》:“鸡鸣发黄山,暝投虾湖宿。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提携采铅客,结荷水边沐。半夜四天开,星河烂人目。明晨大楼去,岗陇多屈伏。当与持斧翁,前溪伐云木。”
后一首将李白与采铅的工人一起风餐露宿以及路途的艰辛等情景都写得非常细致,犹如实录。后来,李白在《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还念念不忘,写道:“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
四
李白曾写了《地藏菩萨赞并序》,又引出了李白与金地藏一段公案。清人孙璧文《考古录》云:“《江南通志》称金地藏名乔觉,暹罗国王子,少落发为沙门。至德初行脚至九华山……今白集中有《地藏菩萨序赞》……白为古地藏作赞,非为金地藏作赞也。”“暹罗国”为古泰国名,显然有误,应为新罗国。“至德”为唐肃宗的年号,只用了两年,至德元年,亦即天宝(唐玄宗年号)十五年,至德二年后,就改为乾元年号了;所以,如果这里的记载是准确的,金地藏来九华山的时间,只能在至德元年,也就是756年,否则不能说“至德初”。这一年,李白五十六岁,这时及之后,李白似乎没有再来九华山一带;所以,李白与金地藏应该不曾谋面。
但是,不曾谋面,不等于没有听说,不等于对这位僧人的信仰一点不了解。我们基本赞同孙璧文的看法,李白《地藏菩萨赞》是为古地藏作,非为金地藏作;但我们不赞同有的学者更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李白的这篇赞并序,与九华山无关,与金地藏无关。⑥这说法太绝对了,有关还是无关,只能说无法确定。你说无关,有可能;我若说有关,也有可能,或许李白首先是知道有金地藏这位高僧,了解他的地藏信仰,然后才接受别人的请托,才作了这篇序赞呢?一孔之见,不揣浅陋,愿就教于大方之家。
注释:
① 郁贤皓《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第二卷《李白论稿》,第549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同上,第568—569页。
③ 参阅赵昌平《鲁仲连、赵蕤与李白——兼论古代文化史、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
④ 郁贤皓《松浦友久李白研究述评》,郁贤皓《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第二卷《李白论稿》,第633页。
⑤ 《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⑥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四,第1638页为这篇序赞所作的按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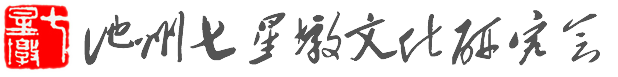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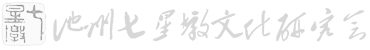
 皖ICP备14013909号
皖ICP备1401390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