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愿李太白
作者:何家荣
一
中晚唐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写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安史之乱”前后,诗仙李白就曾落魄于江南这片神奇而忧伤之地。可以想见,江南看不尽的绿水青山、饮不尽的美酒,一定让身心憔悴的李白得到了安慰和解脱;所以,他才会徘徊流连,久久不忍离去,且最终成为了他人生的归宿。同样可以想见,江南浓郁的佛教气氛,一定潜移默化感染了李白;所以,他与僧佛有关的作品,大都写于这一时期。
唐代是佛教的繁盛期,唐代文人少有不受佛教影响的。但是,唐代文人崇奉的,主要是《维摩诘经》。比如,被人称为“诗佛”的王维,将维摩诘作为自己的名和字;李白自认为是“金粟如来”, 金粟如来,正是《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摩诘经》)中的主角,化身为居士维摩诘。这一点,张海沙《唐代文人与〈维摩诘经〉》一文论述得非常充分,文中指出:
“唐代文人及后世的文人普遍推崇《维摩诘经》,是因为推崇维摩诘这样一位优游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人物。这是中国传统中所不曾有过的、消解了人格上矛盾的人物。被推崇为圣人的孔夫子及真人庄子,其思想体系及日常生活实践都充满着未能解决的矛盾。同时接受儒道两家思想的传统文人更艰难地在入世与出世、济人与自适、个体与群体、有限与无限、精神与物质等矛盾中挣扎。维摩诘的观念与实践是如此地和谐,他以毕竟空观和不可思议解脱解决了困惑无数文人的矛盾。他将对最高真理的追求与平常生活融合、将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外在世界融合。”
李白的情形又似乎稍稍有一点异样,他对于佛、对于佛教似乎并不是一种专注的信仰,而只是一种普泛的兴趣和向往。李白自号为青莲居士,而莲花与佛、道两家都有密切的关联。《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九“西上莲花山”:“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这是道家的莲花。《僧伽歌》:“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亭》:“子见水中月,青莲出尘埃。”这是佛家的莲花。李白自号青莲,也许兼有对佛、道两家的向往之意吧。李白认为是“金粟如来”,但他并没有真的像维摩诘那样,“奉行沙门清净律行”,“常修梵行”。李白到过一些寺庙,但都没有久留;他结识过一些僧人,但都没有深交。李白集中涉佛、涉禅之作不在少数,如《赠宣州灵源寺仲濬公》云:“观心同水月,解领得明珠”、《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其一)云:“花将色不染,水与心俱闲。一坐度小劫,观空天地间。”但李白并没有真正沉静下来参佛、参禅。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吧,对于佛教,李白是不期而遇,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世界的香云、花雨,以及佛的智慧、僧人的闲适、寺院的幽远等,令李白深感兴趣,李白得以在那个世界里暂时安妥他落魄的心灵、迷惘的精神。
二
非常有意思的是,李白还写过一篇《地藏菩萨赞并序》,历来少有人关注,兹引录如下:
大雄掩照,日月崩落。惟佛智慧大而光生死雪。赖假普慈力,能救无边苦。独出旷劫,导开横流,则地藏菩萨为当仁矣。弟子扶风窦滔,少以英气爽迈,结交王侯,清风豪侠,极乐生疾,乃得惠剑于真宰,湛本心于虚空。愿图圣容,以祈景福,庶冥力凭助,而厥苦有瘳。爰命小才,式赞其事。赞曰:
本心若虚空,清净无一物。焚荡淫怒痴,圆寂了见佛。五彩图圣像,悟真非妄传。扫雪万病尽,爽然清凉天。赞此功德海,永为旷代宣。
从这篇序、赞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
一是李白对佛教经典,包括《地藏经》非常熟悉。正因为如此,诸如“大雄”、“旷劫”、“横流”、“惠剑”、“清凉天”等佛典中词语,他能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地藏经》中历用“千劫”、“久远劫”、“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不可计劫”、“过去不可思议劫”、“百千万亿不可说劫”、“四百千万亿劫”等语词,《楞严经》并称为“旷劫”,都是一个意思,即久远之劫也。查《全唐诗》,“旷劫”一词,唯独李白两此使用过,其他诗人(包括皎然这样的诗僧)都未曾用过。
二是李白写《地藏菩萨赞并序》是受人之托,是传达别人对地藏菩萨、对佛的礼赞。“愿图圣容,以祈景福”,是信奉《地藏经》教义的具体表现。《地藏菩萨本愿经》曰:
“佛告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镂、塑漆形像,是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
李白的这篇赞、序,引出了他与金地藏的一段公案。清人孙璧文《考古录》云:“《江南通志》称金地藏名乔觉,暹罗国王子,少落发为沙门。至德初行脚至九华山……今白集中有《地藏菩萨序赞》……白为古地藏作赞,非为金地藏作赞也。”“暹罗国”为古泰国名,显然有误,应为新罗国。“至德”为唐肃宗的年号,只用了两年,至德元年,亦即天宝(唐玄宗年号)十五年,至德二年后,就改为乾元年号了;所以,如果这里的记载是准确的,金地藏来九华山的时间,只能在至德元年,也就是756年,否则不能说“至德初”。这一年,李白五十六岁,这时及之后,李白似乎没有再来九华山一带;所以,李白与金地藏应该没有机会谋面。但另据与金地藏差不多同时期的本土文人费冠卿《九华山化成寺记》记载,化成寺建于至德初,金地藏来九华山的时间应该在开元末;这样一来,李白天宝末来秋浦、青阳一带,金地藏正在九华山上。可能因为李白从来就没有上过九华山,所以无缘与金地藏谋面。
但是,不曾谋面,不等于没有听说过,不等于对这位僧人的信仰一点不了解。我们基本赞同孙璧文的看法,李白《地藏菩萨赞》是为古地藏作,非为金地藏作;但我们不能赞同有的学者更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李白的这篇赞并序,与九华山无关,与金地藏无关。这说法太绝对了,有关还是无关,只能说无法确定。你说无关,有可能;我若说有关,也有可能,或许李白首先是知道有金地藏这位高僧,了解他的地藏信仰,然后才接受别人的请托,才作了这篇序赞呢?
三
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佛祖释迦牟尼如此称扬他:
“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时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时狮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
文殊师利,时长者子因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于彼佛前立斯大愿,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
从此,历经千千万万劫,地藏菩萨屡发弘愿,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具大慈悲,普度众生。于是,地藏菩萨被尊称为大愿地藏王菩萨。
我们没有理由说,李白信奉佛法、信仰地藏精神;但我们有理由说,李白的许多诗篇、诗句,妙合佛法,妙合地藏精神。姑举一例,《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本与僧、与佛无涉,但却通篇妙合《地藏经》精义:
《地藏经》曰: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犹如一座火宅,受生死烦恼无名之火所烧。李诗曰: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地藏经》曰: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尘劫,迷惑障难。如鱼游网,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遭网。李诗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两相比读,便觉别有一种境界、别有一种趣味。
更有意思的是,地藏菩萨屡发弘愿,李白也是屡发弘愿。你看他一会儿要“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永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古风》)“怡然青莲宫,永愿恣游眺。”(《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一会儿要“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一)“心垢都已灭,永言题禅房。”(《安州般若寺水阁纳凉,喜遇薛员外乂》)一会儿要“永愿坐此石,长垂严陵钓。”(《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爱此从冥搜,永怀临湍游。”(《越中秋怀》)一会儿又要“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结心寄青松,永悟客情毕。”(《望黄鹤楼》)“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月下独酌四首》其一)等等。
地藏菩萨屡发弘愿,是欲证如来庄严妙相。李白屡发弘愿,是为了他那飘逸不定的理想。李白一会儿想做狂人,“凤歌笑孔丘”,一会儿又想像孔子一样,做圣人,“垂辉映千春”;他一会儿想布衣干政,平交王侯,一会儿又想适情适性,散发弄扁舟,云帆济沧海;他一会儿想道家的丹液金骨,一会儿又想佛家的空观空有;他一会儿想做个纵情的饮者,长醉不欲醒,一会儿又想做个淡定的烟霞客,看云卷云舒,任花开花落。但是,地藏菩萨为了他的弘愿,“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故名地藏。李白呢,他没有坚守住任何一个弘愿,一切都服从了他那自由飘逸的性情,“大愿”最终都成了“大言”。李白集中,仅“万古”一词,就出现24次之多,别的大言、豪语亦不胜枚举。这一方面,李白自己也不回避,他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无论哪一途,李白最终都没能如愿;所以,李白一次次感叹他的人生是失败的,如:“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其事竟不就,哀哉难再陈。”(《赠张相镐》其一)“才将圣不偶,命与时俱背。”(《赠从弟宣州长史昭》)“叹我万里游,飘摇三十春。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门有车马客行》)
好在李白是天才,他任情性于儒、道、佛、隐、侠,最终都没有成就,但成就了别一方面,那就是“大自在”,那就是他的逸兴、他的诗情。大愿李太白,没能成佛,没能成仙,没能成圣人贤臣,没能成隐者豪侠;但成了诗仙、酒仙、游仙,一样名垂千古。我们,世间的普通人,不是李太白,因此也就学不得李太白,而应该像地藏菩萨那样,坚守自己的信仰,“安忍不动如大地”,执著前行,方有可能成就平凡的人生。
参考文献:
⑴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⑵张海沙《唐代文人与〈维摩诘经〉》,《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⑶周勋初《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⑷李长之《李白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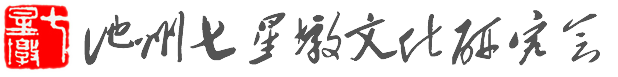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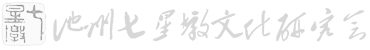
 皖ICP备14013909号
皖ICP备1401390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