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这座古山村
难忘这座古山村
——三访曹村的记忆
丁育民
人生中会有一些难忘的地方,留下一些难忘的事情。地有远有近,事有大有小,能在记忆中留下“难忘”总是弥足珍贵的。且越上年纪,就越发地看重这个“难忘”。
曹村,就是印在我心中一个难以忘怀的地方。
曹村是一座千年古村,名闻遐迩。无论其沧桑的自然风光,还是丰厚的人文景观,都足以使人产生某种巨大的吸引力。我有幸曾三次造访曹村,留下了久远的“难忘”。而今年迈,回忆这三次难忘的亲历,与读者朋友们一道走进这座从远古走来的神秘山村。
沿着周总理的声音
涉水初访“寡妇村”
1965年仲秋。
我刚转业到贵池,就听说贵池是我国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十大重灾区”之一。棠溪公社(乡)的曹村(大队),则是“重灾区”中的“重灾村”。据史料记载:自1940至1949年解放的10年间,全村死于血吸虫病的有610余人,全家死绝的竟达95户。全曹村大队12个自然村,就有8个成了无人村,仅留下32户,幸存的多半是妇女和小孩。当年号称“千户万丁”“小南京”的曹村,变成了闻名全国的“寡妇村”!至今流传着一首悲惨的民谣:“曹村大肚怪,没女肯嫁来。人死没人抬,尸首没人埋。大屋没人住,蒿草没阶台。”成为历史的见证。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关怀苦难的曹村人民,于1957年4月20日在全国血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特别讲到了曹村。同一天,周总理在签发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文件中特别指出:“安徽省贵池县棠溪乡碾子下村(属曹村大队的自然村),百余年前有120户,现在只有曹雨金1户4口人,其中3人仍患血吸虫病。”足见曹村血吸虫病流行何等严重,瘟神何等猖獗!
国务院文件下达后,贵池全县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防治血吸虫病的高潮。县人民政府发给了幸存者曹雨金一个红面烫金的优待证。凭这个证,到医院可免费医疗,到国营商店,可优先供应,生活上给予特殊的照顾,政府还为他修盖了瓦屋。为了拯救他濒临死亡的生命,乡亲们把他抬进城,在县血防站医院做了手术,从他骨瘦如柴矮小身子的肚子里,割出了一个9斤多重的巨型脾块!他的“大肚子病”奇迹般地好了,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果真枯木逢春,他还添人进口生了孩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当我得知这一感人事迹就发生在本县曹村时,心中无比激动,出于职业的习惯,顿时萌生前去采访的念头。于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第一次下乡,就选择了曹村。
——沿着周总理的声音来到这座深山里的“寡妇村”。
曹村远离县城百里之遥,交通十分不便,信息十分闭塞。我搭乘农村班车(一种老式的带蓬布大卡车,车箱里安了几排长条木板作坐位),冒着深山里酷热的“秋老虎”,来到棠溪公社所在的下留田。“留田”沿河分上中下三段,这里称作“下留田”。下车去下留田,要过卵石成滩的龙舒河(俗称“棠溪河”)。河上架着一条摇摇晃晃的木板桥,穿过河心一片乱石滩小岛,桥显得特别的长,人在桥上每走一步,桥身上下“吱吱”作响,虽说有点吓人,但四周风光秀丽,却又令人心旷神怡。
下留田,是一条极古老的山村小街,白天比较冷清,据说每逢晴天清早,周边山民踏着露水来此赶集,等日头爬上山顶,地上青草叶子尖的露水一干,赶集的山民们就一个个回家吃早饭,下地干活去了。故有“露水集”之说。集上山区土特产满街都是,琳琅满目,价钱十分便宜。这时正是鲜枣上市的季节,我从没见过这么大个儿的新鲜枣子,一个个胖敦敦的,绽满了丝丝暗红色的裂缝,只卖八九分钱一斤。
我找到公社,说明来意,当班的说,今天太晚了先住下,明天一早公社派人送你去曹村。我被安排在小街顶头一家小客栈住宿,住在二楼的一个单间里。小客栈是不是公社的招待所?我记不清了。店里十分清闲,那天除我之外,我没有见到什么住店的客人。山里人朴实,给我的感觉非常之好,店面清雅,客房整洁,服务也很热情。
山里确实闭塞,偏僻小街,古风淳朴,但绿水青山,真可谓“秀色可餐”矣。
山里的夜,特别的宁静,窗外不知什么鸟一声声清脆的叫声,非常悦耳。“鸟鸣林更幽”,心底萌生一种神秘和悲凉,难以入眠。我轻轻推开小楼古老的雕花木窗,清凉的月光挟着习习的山风裹着朦胧的景色迎面涌泻进来,顿时一股清清凉凉的爽快袭上心头。
月光下,那条流淌在鹅卵石上泛着点点星光的龙舒河和河面上那座令人胆颤心惊的长长的木板桥,在朦朦胧胧的远山近水的衬托下,勾勒出一幅淡淡的水墨画。那分明是我宜兴老乡吴冠中先生的画风和神韵,令人赏心悦目,陶然欲醉。泉鸣鸟啼给窗口水墨画染上了音乐的色彩,格外动人。我品味了生平在皖南山区第一个恬静的夜晚,令人长久神往……
第二天清早,公社来人喊吃早饭。我习惯把早餐称作“早点”喝稀的。小客栈老板娘端上来的却是新煮的热腾腾香喷喷的新米干饭,我问有没有稀饭?公社来的小伙子认真地对我说:
“进山一定要吃饱。今天我们要赶路呢,再说山里人什么时候吃中饭没定规的。碰上大队干部下小队上了山,中午饭什么时候吃就难说了。浇点菜汤,吃。”
哦,原来还有这档子事。于是我放开肚皮吃了一大碗,还啃了两个包娄(玉米棒),真正撑了个饱。
从下留田街到曹村是没有公路不通班车的,全靠两条腿走。公社小伙(真是抱歉得很,时隔四五十年,他的尊姓大名我居然一点都想不起来了)骑一辆加重自行车带着我在黄土路上飞驰,一路上有说有笑。途中要过一道水流湍急的滚水坝,公社小伙抱歉地笑道:
“冬天枯水时,自行车能骑过去的,现在是发水季节,就只有下河摸水了。讨厌的是,偏偏这个时候是血吸虫流行季节,河里的水说不定就是疫水哩!……唉,不知什么时候能通汽车就好了。”
“嗨,哪有那么巧,疫水就偏偏让我们碰上了?走。”我说着脱下凉鞋,先下了河。
“不过,医生说疫水都在死水里,这儿是活水,没事的。”公社小伙扛着自行车,一边安慰我,一边也下水跟了上来。
我摸水到了对面,先一步上了岸,套上凉鞋,接过他肩上的自行车,趁他结球鞋带的时候骑上了车,喊:“快,上来!”小伙原想客气一下的,见我骑自行车的把式不比他差,就顺从地坐上了后座。
来到曹村,迎面又是一道卵石成滩水流湍急的龙舒河,由东向西横卧村前;又是一座长长的摇摇晃晃的木板桥跨河而立,远远望去,这桥仿佛不像是用来过河行路的,倒像是画在这儿的,给隔河的古村凭添了些许神秘。
进村,公社小伙把我介绍给了大队支书田茂生同志,就骑车匆匆回公社去了。
田茂生是个老支书,是位热心人。他领我在村子里兜了一圈,沿河那条破败的古老“半边街”,格外显得凄凉。街面店铺依稀,古屋鳞次栉比,记载着古村历史的辉煌。石库门,石台阶,门柱上方有戗檐砖雕,下方是长满青苔的麻石墙根,面墙上挂着残缺的雕花砖窗,女儿墙头长着稀疏的荒草,在半空中迎风抖动。临水一溜石板路和巨石垒砌的河邦,仿佛是飘落的历史碎片,嬗变为一页页文化符号,使那些曾经自豪和心酸的历史细节变得虚无而永恒。
我想先去采访曹雨金。这是我的初衷。
“不急。您老远从城里来一趟不容易,在我们这里多待几天。曹雨金家在河南面碾子下村,明天我陪你去,今天先在大村(曹村)里看看,采访采访。”
朴实敦厚的老支书善解人意,已经为我作好了安排。
我们在村中串门,走访了一座又一座陈旧的祖传庭院。尽管格局各有不同,却家家古风依然。虽说许多庭院早已人去楼空物是人非,却仍显示着当年主人的华贵气派。我踏着深巷里青石板上一朵朵岁月的斑痕,仿佛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偌大一个古老的村庄,古街古巷,古色古香,若不是田支书领着向导,我是断然摸不清东南西北的。
前不久才下过一场雨,庭院中小天井里的大岩石上和青砖花台的泥土都湿漉漉地冒着雾状的水珠儿。老支书用一根小树枝,在花台墙角落里拨拉出一粒干死了的小钉螺,对我说,血吸虫病厉害,都是这些小东西作的怪。人民政府号召: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送瘟神,打的就是消灭这些钉螺的人民战争呀。可是这些小东西古怪得很,把它晒干了,见水就活,入土就生(繁殖),灭螺任务艰巨着呢!田支书的讲解,使我第一次弄清了“血防”和“灭螺”的关系。又在他的热情向导下,我见到了“寡妇村”另一位血吸虫病的幸存者——曹悟学。
曹悟学,原有弟兄4个,在旧社会,瘟神夺去了他3个哥哥和父亲的生命,留下他这根独苗,也患上了严重的“大肚子”病,危在旦夕。解放后,人民政府送他到县里治疗,1953年他就在县血防站医院病房里过的春节,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1954年春节,曹悟学这个死里逃生的翻身农民,怀着无限深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在欢庆新中国第5个华诞时,幸福地成了家。我举目四望,他家里装修一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正开心地交谈着,他的爱人郑满芝笑呵呵地捧出了花生、瓜子、米糖和香茶,古老的堂屋里,洋溢着欢声笑语……
正当聊得起劲时,大队文书急吼吼地跑来报告,说公社通知,县里来电话要我立即赶回去,说是要上省城观摩“乌兰牧骑轻骑小分队”的表演。今晚回公休息,明天一早搭班车回城。我还是部队的习惯,奉令即行,说走就走。田支书深情地说:“省里回来后,一定再来呀。”年轻的大队民兵营长骑车送我去公社。走过村前长长的木板桥,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经过树林边一幢孤伶伶的阁楼后门时,听到有人喊:
“下晚了,还去留田街呀?”
“哎,送县里同志呢。你吃晚饭啦?”民兵营长一边骑着车,一边答着腔。
“嗳,正吃着呢。”说着一个个子矮矮的男子把手里的海碗举起来“叮叮”地敲着响。
我问:“谁呀?”
“老雨金欧。”
“什么,是曹雨金?”我惊讶地追问。
“就是他哟,命大着呢,连周总理都晓得他。”
“哎哎,停一停,我去见见他。”
“天不早了,下趟来我陪你去找他。”
我想人家民兵营长连夜还要赶回来呢,就不便强求了。
哪知这次失之交臂竟留下遗憾。等我从合肥江淮大戏院观摩回来,池州地区文办主任马唯一同志指派我参加老作家陈登科在青阳举办的创作班子,接踵而来的是“文革”动乱,直到1973年曹雨金去世,我都没能见到这位曾经得到周总理关怀的幸存者一面……
这次,我沿着周总理的声音初访“寡妇村”,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曹村之行。
觅诗仙游踪
踏雪寻访白笴陂
1982年年初。
我从安庆调回贵池报社。贵池,自古是池州府治所在的一个县;而池州,作为州府一级的政府,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的需要,曾经历了建了撤,撤了建,撤撤建建的多次波折。这时,正值被撤之际。然而池州名人辈出人文荟萃文化底蕴非常丰厚是“撤”不了的,我惊喜地发现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是池州的大功臣。他“五游秋浦(今贵池)”“三上九华”留下50多首诗歌,著名的组诗《秋浦歌十七首》堪称代表之作,引得历代诗人名士踏踪而来,赋诗歌咏,池州因此获得了“千载诗人地”的桂冠。
回顾千年历史,说李白是“千载诗人地”的千载诗人们的领军人物,是当之无愧的!有时我常常这样设想,如果秋浦少了李白,虽然它依然风光秀丽景色迷人,却少了许多灵气,更少了千年的名气;如果秋浦河少了李白呢,虽然它依然“碧水长似秋”“水色异诸水”,却少了历代许多接踪而来的诗歌,也很难成为一条“流淌着诗的河”;甚而至于,我想如果九华山少了李白,至今恐怕还叫着“九子山”这个俚俗之名呢。总之,如果没有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李太白老人家“五游秋浦”、“三上九华”,池州要享有“千载诗人地”的美誉确实是很难很难很难的呀!我真想像不出,如果池州真的少了诗仙李白的话,秋浦、九华山这方钟灵毓秀的奇丽山水那一千二百六十多年是怎么度过的呀……
是的,我深深地爱着这方诗化了的土地。我想以李白在秋浦的诗歌为线索,寻访李白在秋浦的游踪,既填补了我国研究李白中在秋浦的一段空白,又可以为池州改革开放开发人文景观发展旅游事业提供一些可信史料,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的这一构想和心愿,得到了我的两位老友张渭德同志(时任县委宣传部长)和张子文同志(副部长兼总编)的热情支持。于是,我作出了具体的考证计划,绘制出《李白五游秋浦游踪图》,按图逐个寻访,实地考察论证,撰写系列文章,先在《贵池报》副刊上连载,再结集出版。
言归正传,曹村因瘟神肆虐变成了“寡妇村”,天下闻名;唯曹村是李白笔下的“白笴陂”,却鲜为人知了。
为此,我作了专门的考证:白笴陂,因盛产笴竹而得名。又因笴竹积雪,才被李白称作白笴陂。当年李白来的时候,白笴陂尚是荒郊僻野,杳无人烟。
至于白笴陂为何易名曹村呢?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头说起。最近,我有幸访得刘街乡缟溪曹(俗称“缟溪曹家”)曹氏家族的第三十七世裔孙曹季泉先生。他是一位热衷续编《曹氏宗谱》的乡贤文士,向我热情地出示了珍藏的清乾隆甲申年版《礼和曹氏宗谱》(即曹村的《曹氏宗谱》)和清光绪丙子岁重修《曹氏宗谱》(这是一部涵盖曹村曹氏各支宗脉的庞大的宗谱),方始我进一步理清了曹村历史变遣的来龙去脉,竟然与一桩惊心动魄的历史冤案相关连。
北宋名臣、曹氏五世祖曹利用,在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侵时,真宗皇帝赵恒授以阁门祗侯、崇仪副使作为朝廷的全权代表,负钦命,赴澶州(今河北濮阳县),与辽议和。曹利用凛然有节,据理力争,不辱使命,皇上大悦,连连加官进爵,擢枢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天禧三年(1019),拜枢密使执政官与宰相;乾兴元年(1022),以左仆射武陵军节度使进景灵宫,封韩国公班宰相。因他一向执法公正严明,得罪了中宫和一些奸佞大臣。真宗驾崩,仁宗赵祯即大位,太后用事,真乃“一朝天子一朝臣”,于天圣七年(1029)正月,因曹利用的侄儿曹汭酒后戏穿黄袍,中宫内侍罗崇勋以旧恨奏帝,遭罢枢密使,旋降为千牛卫将军,再贬为崇信节度使,又贬至房州(今湖北房县)。这还不甘心,又指派酷吏内侍杨怀敏押送,途经襄阳驿站,以恶言百般凌辱,刚正不阿的曹利用,不屈自缢而死。时为二月二十五日,享年67岁。临终遗言,循循告戒:“吾思至此,儆尔子孙,宜求田问舍,敛迹埋名,韬遁为上计。”其长子曹清(字立甫,号立原),时任同平章事出守福建泉州知州,受父株连,降二秩,贬江州(属江西)彭泽知县。慕李太白之名,感陶靖节之风,“解绶挂冠,隐迹贵池”。途中过玉壶洞慨然题七绝一首,表达了他断绝仕途的决心。诗曰:
洞前流水碧如苔,
洞口桃花扑面开。
转头望断情难断,
长啸一声不再来。
曹清来到贵池深山白笴陂,见白笴山上笴竹如云,龙舒河畔景色殊胜,“卜吉于震峰之下”,遂遣家栖隐至此。易白笴陂为“怀陶里”,改白笴山为震峰山。造礼和堂,为曹氏一脉之发祥之地。“潜身震峰山下,安居礼和(堂)。插柳种花,赋诗饮酒,耕于田,钓于河(龙舒河),远效靖节,自号怀陶里人。”赋七绝《怀陶》诗曰:
何处乾坤可著余?
震峰山下且安庐。
山茶喷火五柳秀,
谁辨当年陶令居。
(引自清乾隆甲申年版《礼和曹氏宗谱》卷首)
《江南通志》有曹清“朝廷屡征不起,子孙遂世居于此”的记载。因而,曹村古名白笴陂,从此称作“白笴村”,俗称“笴村”。于是,在曹氏家族中排行第六世祖的曹清,就成为曹村曹氏宗脉的始祖了。实际上,他也是贵池曹氏家族的始祖。按庄子“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的理论分类,曹清公这位曹村曹氏的始祖尚属“小隐”之列。清《光绪贵池县志》有“白笴陂,一在城南八十里,李白游览处。宋彭泽令曹清移家于此。今有曹村,亦名怀陶里”的记载。一次曹清去池阳郡(即池州)府城回笴村时,赋七绝一首《自郡泛舟齐山(湖)归家》,诗曰:
十里平湖漫不流,
晓风吹浪打行舟。
定知归行浸灯火,
家在秋浦最尽头。
诗中“平湖”,即李白《秋浦歌十七首》中“水如一匹练,此地即平天”的平天湖。诗人抒发了身居深山、远离府城闹市悠然自得的心情。
笴村因龙舒河经常泛滥成灾,曹氏家族筑堤防洪,围垦造田,故怀陶里又有“白笴堰”之雅号。后来曹家人丁兴旺,成为一方名门望族,才唤作“曹村”至今。这就是曹村的来历。
于是,古时名唤“白笴陂”的曹村,成为我考证李白在秋浦的第一个游踪。
这一年(1982年)的春节前夕,江南喜降瑞雪,更增添了节日的气氛。因当年李白也是踏雪来到白笴陂的,所以我特意也选择了这场大雪进山访曹村。
这时棠溪公社驻地已不在下留田街了。早在1971年搬到了龙舒河北边的庄村姚。根据毛主席老人家“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出于战备的需要,皖南山区一下子建起了许多“小三线”军工厂。一时间,“好人好马上三线,千军万马大搬迁。”数万民兵师、民兵团,开山筑路,硬是肩挑镐刨,开通了深山公路。继之,大批身怀技术的上海人,浩浩荡荡开进了贵池深山,搬来了大批机器设备,山沟里工厂星罗棋布,平地而起。当地乡民从古到今,哪见过这等阵势,惊称“小上海”!深山荒野一下沸腾了起来,也越发地神秘了起来。
山里变了样,我这次冒雪进山,又是第一次来到变了样的棠溪公社。接待我的是公社书记吴成贵同志,此人我久闻大名。他性格豪爽,为人仗义,乡间戏称“吴大帅”,颇有名气!他听说我要去曹村考察李白游踪,大为高兴。不巧的是他刚刚接到通知,要他连夜赶到县里去开会。我忙对他说:
“吴书记,您忙您的去,公社派一位同志给我带带路就行了。”
“哪怎么行!”“吴大帅”嗓门大得吓人。说:“你是来帮我们挖宝的。再说,大过年的还下着雪,说什么我也得亲自送你去。”
那时农村人民公社没有汽车。“吴大帅”就是“吴大帅”,说到做到。他从附近三线厂借来了一辆带篷的北京吉普,冒着鹅毛大雪,亲自开车送我去曹村。
江南的雪,再大也没有“北国风光”那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观豪情,有的只是轻歌曼舞的温馨和浪漫。“大帅”开车的本事,本人实在不敢恭维。一路上,小吉普一冲一楞一蹦一跳地活像喝醉了酒的手扶拖拉机。笑道:
“‘大帅’呀,你不过年,我还想过年哩。你可得稳着点儿。”
“哎呀,就你们这些文化人性命金贵,我保你太——平——无——事——欧——!哈哈……”
他幽默地学着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维持会长”敲更喊话的腔调,引得我一路欢笑……
车到曹村,“大帅”将我交给了年轻的大队支书王荣跃同志,如此这般地与王支书“咬了一阵耳朵”,交待了一番,调转车头,风风火火地赶回去了。
王支书是个热情人,又是个有些文化修养的人。他对我来考察李白游踪特别热情,为我细心安排,全程陪同。当晚,安排我住在村东头一座围墙里的小平房里。这里是大队的豆腐坊兼招待所。夜晚,王支书打着手电领着我踏雪进村,穿巷走户,采访一些有点文化的老人。所谈主题:就是李白。
访谈中,沿河边一家古屋里,意外地遇见了县医药公司的老友“大胡子”方泰来同志。原来他已调曹村村东头的县养鹿场工作,还做了曹村的上门女婿,成了一个真正的曹村人。他对我来考察李白游踪,非常高兴,一再说有什么要他跑腿的,尽管吩咐。
翌日清晨,雪霁初睛,古村银装素裹,分外妖娆。王支书陪同我踏雪探幽白笴陂,寻李白游踪。从我住的豆腐房到白笴陂,沿着龙舒河北岸,由村东头到村西头,整整穿过了古老“小南京”的半边街。青石板上铺着厚厚的积雪,河边上结着薄薄的冰凌,清凉的河水在鹅卵石铺就的河床上流淌,泛起历史的涟漪,古村越发显得悠远安详。一路上王支书不住地提醒我,小心脚下滑。来到村西水口龙舒河的拐弯处,一座披着皑皑白雪的玲珑小山,俗称“狮形”。山上山下古木森森长满着一丛丛积着白雪的青青笴竹。
哦!白——笴——陂。
说到李白与白笴陂,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李白为何冒雪进山来到这里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作了专题考证:李白是受青阳县令韦仲堪(字权舆)之邀,去找隐居秋浦石门桃花坞的高霁(字暄之),三位诗友结伴同行,踏雪上九子山,在白沙岭古道途中,合作著名的《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并序》一诗。真可谓一字千金,万古流芳。这首诗被誉为九华山的“定名篇”。因而,李白这次冒雪进山,途经白笴陂上九华山之行,正是李白在秋浦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行动,早已载入史册。(见本人著由黄山书社1989年8月出版的《李白游秋浦》、由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李白与九华山》)
李白来到白笴陂,留恋这里的雪后风光,夜宿岩穴,饱览月下雪景,饮酒吟诗,萌生思乡之情。即兴赋《游秋浦白笴陂二首》,千古绝唱,唱响了这个秋浦深山里的白笴陂。诗曰:
其一
何处夜行好?月明白笴陂。
山光摇积雪,猿影挂寒枝。
但恐佳景晚,小令归棹移。
人来有清兴,及此有相思。
其二
白笴夜长啸,爽然溪谷寒。
鱼龙动陂水,处处生波澜。
天借一明月,飞来碧云端。
故乡不可见,肠断正西看。
有道是流水掬不住,时光捉不住,青春留不住,但是李白的诗歌留下来了,永远定格在秋浦的青山绿水之中。他那动人的笔调,把我们带进了一幅千年不褪色的月色皎皎、夜雪如玉、白猿飞跃、蛟鱼戏水、石老云荒的画卷之中。可见诗境和风景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诗中可以读出白笴陂,白笴陂也能长出诗来。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白笴陂山不高,龙舒河水不深,只因李白涉足留诗而名垂青史。白笴陂的记忆,至今成为李白遗留在秋浦的古迹群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名胜之地。身临其境,让人感到一种褪却了俗尘浮华返璞归真的超然境界。
王支书对我说:“吴书记交待了,您是专程来考察李白的,叫我一定要好好陪你多看看。这狮形山我小时候经常上去,上面有许多景致呢,就是没有路,今天我们先上去看看怎么样?”
王支书的话越发鼓舞了我,欢欣地说:“好,上!”
临上白笴陂小山,王支书在山脚社员家借了一把砍刀,热情地在前面斩荆扫雪,开出了一条登山之路。脚下踩着松软的枯枝落叶上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头顶上碰落树枝树叶上的积雪,纷纷扬扬的雪沫,随着寒风钻进颈脖衣领口,化成冰冷的水珠灌进背心,与汗水融合感到一种透心的凉爽。我看着前面大汗淋淋的王支书,心中无限感动,他却回过头来说:
“让您吃苦了。”
我忙答道:“你可知道,当年李白来白笴陂的时候,也是踏雪来的。他的诗就是写这里的雪景。我们今天也踩着雪上白笴陂,正好能领悟李白诗中雪的意境。真的应当感谢老天,给了这场大雪,我们才有幸能见到雪中白笴陂的真模真样来呢。”
登上白笴陂山顶,放眼一望,波光粼粼的龙舒河,雪野茫茫的古曹村,尽收眼底。我蓦地悟出龙舒河与白笴陂在风雪的背景下搭配,真正具有了诗的韵味。环顾山巅,又是一个神秘的冰雪世界。王支书对山顶景观,如数家珍。华盖峰巅,雪缀奇岩,森罗万象,有芙蓉岫,攀鸟道上太空岩,积雪更厚,坚冰如铁。据清《光绪贵池县志》载,此处当有瑶珂阁,“矗立崩岩,无杯土所依;森森古木,根株抱石,藤须交织,拏云攫雾,险夷非凡。”爬上极顶,有朝天洞。奇哉怪耶,山顶有洞,俗称“亮洞”。据说古时洞内可摆4张八仙桌,是神仙聚会之处。文化与历史在这里珍藏,距离世俗如此遥远,今日想来,虚无飘渺,宛若梦境。古人曹敬贻有:“神区奥境,难描摩天然邱壑”之赞叹。(值得关注的是:白笴陂山顶上这一片原始奇景,至今尘封云乡,无人问津,实为可惜……)
下山来到白笴陂向阳的南山麓,由西向东,有文昌阁遗址、“三阳庙”庙基。何为“三阳”?据说宋代天下咸阳、襄阳、池阳(池州)三郡最有名气,号称“三阳”。峭崖陡壁下,依次罗列着李白仙踪名胜:一座长方形的岩穴,上有爬满青藤积着白雪的岩顶遮风挡雨,下有平坦岩台,宛如大牀,“牀”沿下有岩阶踏足置屐。相传,这就是当年李白露宿白笴陂的睡卧之处。掀开藤蔓,岩壁上露出醒目的“太白石牀”四个隶书大字。“太白石牀”依山傍水,宽敞平正,端坐“牀”沿,可赏东南半空中“月峰弯玉盘徐升”的奇观。李白诗中“何处夜行好?月明白笴陂”,“天借一明月,飞来碧云端”的诗句,正是描绘此处夜景的神来之笔。奇怪的是“石牀”周围一丛丛四季常青的笴竹,散发出悠悠酒香,令人未饮欲醉。传说酒仙翁李太白当年在此赋诗饮酒时,不经意将酒洒落笴竹叶上滴进山泥竹根,从此留下了奇异酒香,千年不消。
由太白石牀向东丈余,山腰上有一幽深溶洞,人称“青莲洞”。洞口不大,躬身可进,入洞十余米,豁然开朗,石柱、石莲、石钟乳,形状怪异,琳琅满目,再往前则深渊莫测矣。洞口旁高三丈余的峭崖上,有一座高高的岩台,相传李白曾在此饮酒放歌。据村中老人们说,峭崖上也刻有字,可惜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也被青苔枯藤深深地掩埋湮没了。说来真巧,这时“大胡子”方泰来肩上扛扇杉木梯子,身后跟着一个小男孩,一手拎只小桶,一手拿把刷子,是“大胡子”的儿子小方明。父子二人兴匆匆地赶来了。“大胡子”爬上梯子,剥开藤蔓,用刷子清除崖上的青苔,醮着小桶里的冰水,细细清扫,高高的崖壁上,顿时显出了“太白长啸处”五个斗大的摩崖石刻来,字迹遒劲隽丽,古风扑面。相传这“太白长啸处”和“太白石牀”几个字,出自晚唐会昌年间出守池州刺史的著名诗人杜牧之手,也有说是宋代处士曹清的墨迹,究竟何人题刻?实难定论矣!
难得的是“太白长啸处”、“太白石牀”和“青莲洞”以至整个白笴陂,至今依然那么自然那么古朴,没有商业运作古文化的那种变形变味的矫情。这些骨子里蕴含着朦胧诗般书卷气的景观,不经意营造了一方诗化了的名胜。据王支书的介绍,古时曹村人民为了纪念李白,特地在白笴陂东山脚下的入口处,建造了一座太白祠,明末毁于兵燹;后又在祠基上建起了一座曹氏家庙,仍以李白之号命名:“青莲庵”,又毁于“文革”,庙基废墟已沦为农家菜园。清代曹村乡贤曹文慧(字智珠)赋五律《太白祠遗址》。诗曰:
白笴千峰里,飞来皎月光。
相传唐李白,此处旧祠堂。
路断苔痕古,诗磨石篆香。
风流呼欲出,溪水共徜徉。
尚有晚清诗人张公锡蕃老先生留下的五律《白笴陂丹谷原韵》传世。诗曰:
迹自青莲著,陂还白笴传。
胜情成独往,芳躅继前贤。
夜对樽前月,朝携槛外烟。
何时随子去,亦学饮中仙。
——以上二诗,引自清《光绪贵池县志·卷三·白笴山》古人为李太白在秋浦白笴陂游踪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有力的佐证。
这次白笴陂寻李白游踪的专访,所撰 “李白游秋浦”系列考证的首篇文章,题曰:《长啸白笴陂》,刊载于1982年7月3日《贵池报》副刊,为我踏雪二访曹村画上了一个难忘的句号。
美国姑娘访曹村
圆了一个李白梦
1985年4月中旬。
我专为陪同一位醉心李白的美国姑娘考察秋浦白笴陂,第三次造访曹村。
这位美国姑娘还有一个中国芳名,叫“方葆珍”。她原是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古代汉语研究生,专攻李白诗歌,已具较深的造诣,去年9月,来复旦大学进修的美国高级进修生。可贵的是她对诗仙李白怀有深厚的崇敬之情。她说中国的古典诗歌太丰富了,太深奥了。她这次来中国深造,决心实地考察李白的游踪,寻找李白诗歌的出处,更深入地领悟伟大诗人李白诗歌的原意,加深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解。这次古秋浦之行,用她的话来说:“是来圆李白梦的。”与她一起来考察的有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部的年轻教师凃秀兰小姐。她们俩结伴同行形影不离亲如姊妹。县里安排我陪同她们,负责向她们介绍李白在秋浦的诗歌及其游踪,并解答她们提出的有关问题。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池州这个地方,比起东南沿海那些开放城市显得就很闭塞,来的外宾很少,偶有所见,十分稀罕。因而,在对待接待外宾的事情,仍怀有几分“敏感”,要求十分严格。所谓“外事无小事”,足见何等重视,也反映了我们中国人的好客与真诚。尽管只来了一个才27岁的姑娘,因为她是来自大洋彼岸碧眼金发的美国姑娘,安庆地区外事办(当时贵池县隶属于安庆地区)和贵池县人民政府外事办,为接待她专门下达了一份“机密”文件,作了热情周到的安排。记得前年(1983年)9月初,“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访华团”团长、著名的研究李白的学者松浦友久教授,率领一行12 位学者前来考察李白在秋浦的行踪和诗歌,组织上也是安排我作主要接谈人。当时限定他们只到齐山、平天湖,万罗山李白钓鱼台、逻人石等县城周边地方进行考察。深山里那些李白游踪,尽管松浦友久先生一再向我提出要求,终因地处保密的小三线军工厂所在,未能得到满足;而这次方葆珍小姐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改革开放更深入了,三线厂也已转为民用厂了,才开始向外宾开放曹村白笴陂。方葆珍小姐成为曹村有史以来接待的第一个外国客人。
按考察日程安排,4月14日一早,我们驱车进山,由远而近,在地区和县里以及棠溪乡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第一站就直奔曹村。车就停在白笴陂东山脚下青莲庵遗址处。一边是绕山九十度拐弯的龙舒河,波光粼粼,清澈见底。河畔巨大的古树林遮天蔽日,幽深静谧;一边是郁郁葱葱的白笴陂,青翠欲滴。优美的风光,自然的生态,清鲜的空气,荡涤了胸中都市的浑浊。方葆珍小姐伸开双臂,放声欢呼:
“啊!真是太美了!李太白真是太有眼力了!”
我乘兴向她们朗诵了李白《游秋浦白笴陂二首》,并以诗说景,讲到了李白雪夜露宿的“太白石牀”,讲了李白放歌的“太白长啸处”,讲了幽秘的“青莲洞”,讲了已毁的太白祠、青莲庵,讲了李白因何踏雪来到这里,讲了源渊流长的龙舒河,讲了曹村的千年变迁,还讲了诗人怀乡思亲之情……
方葆珍小姐感慨地说:“李白太伟大了。他不但是中国的伟大诗人,也是世界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长上了翅膀,飞过大洋,飞进了我的心里。我最早背诵的李白诗歌就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七绝《静夜思》)”说着她一下坐到了太白石牀上,一手拍着“牀”沿说:“呵,我真想带顶蚊帐来,在这张李白老人家睡过的石牀上,住上十天半月,天天观看唐朝李白曾经看过的秋浦月亮!”
美国姑娘的豪爽和浪漫,引起大家一片欢笑。这无疑是联想的功能效应。人的联想往往是很厉害的,诗人的联想能吟出美妙的诗句,音乐家的联想会产生动人的旋律。也许是李白诗中“人来有清兴,及此有相思”的诗句,触动了方小姐思乡之情。她告诉我,她是犹太人血统,她的姑妈姑夫、姨妈姨夫都是犹太人,二战时在波兰,都惨遭德国法西斯杀害了……
“想想他们,我真是幸运极了。”方葆珍小姐陷入了深沉的联想……
我告诉她,她确实是很幸运的,她是有史以来访问曹村的第一个外国客人。
话音一落地,这位身高马大长发披肩的美国姑娘一下蹦下太白石牀,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迪斯科,嘴里还一个劲地欢呼着:
“哦!我真幸福,我该是外国人中最值得骄傲的人了!”
她说着,一定要我和她们在太白石牀前合个影。她说她要带回去作纪念,告诉她的亲人朋友和她未来的先生,这里是伟大诗人李白笔下的白笴陂,这里是诗仙睡过的太白石牀!……
时近晌午,中饭在哪里吃呢?回城路太远,到棠溪乡政府也有一段路程,还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吕德来想了个点子,由村支书王荣跃安排在村民组长许长贵家中吃午饭。他家就在曹村东头靠河边一幢新建的楼房。在他家设家宴款待外宾,既热情且方便,又不失礼仪,还可以让外国客人亲眼看看我们改革开放的新农村。
一桌丰盛的“山村农家宴”就摆在了新楼上。龙舒河里的石斑鱼、泥鳅、石鸡,山头上的竹笋、香椿、马兰、石耳、香菇……色香味俱全,乐得美国姑娘连声说:
“山好,水好,风光好,诗歌好,人更好,谢谢李白,谢谢曹村!”
在离开曹村时,方葆珍小姐从车窗口眺望着古老的山村,眺望着充满古典诗韵的白笴陂,双手紧紧抱着同来的凃秀兰小姐深情地说:
“哦,我们真的不虚此行啊,圆了我一个向往了很久很久的李白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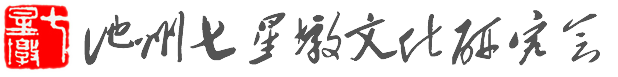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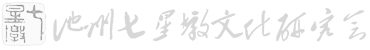
 皖ICP备14013909号
皖ICP备1401390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