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阳县谢家村风流探源
谢村聚落似园林,历史渊源底蕴深。络绎人文如累叶,风流有自住春音。
——题记
谢家村座落在皖南山区青阳县陵阳镇沙济的琉璃岭下,北距青阳县城40公里,南由合(肥)黄(山)高速连接黄山,是九华山的一座南大门,是谢氏聚族而居的大村落。
提起谢家村,也许大家并不陌生,196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董必武曾陪同越南胡志明主席前往黄山,途经陵阳镇谢家村时,看到谢家村依山傍水,景色旖旎,民宅尽是青砖小瓦马头墙,古色古香,古韵厚重,他深有感触地说:“过陵阳镇恺帆同志(安徽省副省长)语我,此地流传有“富贵阳陵阳镇,风流谢家村”之说,以诗纪之”。
道傍听传说,具体不烦言。富贵陵阳镇,风流谢家村。乡居皆瓦屋,聚落似林园。抗日遭蹂躏。生涯有复翻。人民新作主,扫除旧巢痕。
此诗曾在当时《合肥晚报》和当年5月21日《羊城晚报》同时发表,这使陵阳镇谢家村的名气,又一次闻名遐迩了。
至于这一口碑的流传,究其“风流”之源,始于何时,传说纷纭,莫衷一是。
2008年之秋,我们乘车前往陵阳镇谢家村,作了一次走马观花的探访。
一、谢村聚落似园林
今乘秋爽访园林,满畦黄花满地金。所谓“园林”却正是董老所说的“聚落似林园”的谢家村。我们去谢家村是由陵阳沙济的桥头店过桥,沿其沙堤古陵阳河东行,河水平缓而清幽,秋水逐人来的呼唤魅力,将我们牵引到了谢家村。抬眼望了望这疑似含烟又隐掩的景色,若似迷离而杳然的村子,顿然想起“风流”自斯来的传说。一阵清风掠过,沙沙的脚步声,伴随着秋天的脚步,我们踏进了风流谢家村。
陵阳秋色数谢家村最好。它除了村前桥畔浓荫色,一片清溪映玉痕之外,立在溪边可纵目远眺,那屹立在村东的黄金峰,峰高石峭,层峦叠翠,其“烟雨滴空翠,壁立千悬峭”的巍峨景观,历历在目。黄金峰它连脉于泾县桃花潭和赤林渡上的挹秀峰,清隐峰,逶迤西纵,由贵池石门的桃花坞蜿蜒北入九华山,横亘数百里,四围碧野成城,将陵阳团团围住,故陵阳有盆地或狭谷长廊之称,可说是钟灵毓秀。谢家村的东麓岭下苏和东南部的广阳(陵阳县一度避讳有广阳县之称),即是清弋江的源头(今之太平湖)。清弋江是条南北流向的山川,南极乃是谢家村的琉璃岭峡谷,那里“漱玉染翠色,锦秀蕴其中”。所谓“漱玉染翠色”,即是谢家村据有灵山秀水,山水形胜的自然生态优势,得天独厚的园林本色,是一座赋有“锦秀蕴其中”的聚落氏族。这里的佳山胜水,引来了一段古老历史的轶闻。传说中国第一位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曾来到这里,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青阳县谢家村风流探源(2)
谢家村地处徽商的营运范围之内,是徽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所谓徽商,最先始起于歙、黟、休、绩、祁、骛六个县,在其不断开拓的进程中,从它们地处狭窄的徽州府,走向长江两岸,乃至全国各地,于是在较大而又集中的区域内,把那些以连亲带故的为纽带的乡族邻里关系和那些分散、零星的一些世交朋友组合起来,便是“徽商”这一名称的泛称。陵阳镇、谢家村这一带人也可称是“徽商”之裔。
陵阳和谢家村人,都具有一种维系凝聚家族的亲和力和奋进力,他们把积赚的钱财带回家,买田造屋,既为家人和自己的享受,为子孙造福,也作为自己事业成功的标志。不管外地如何繁华,一种“慎终追远”,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谢氏极大多数人的思想上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谢家村村落建筑都具有聚族而居的特色。
谢家村是一处百户以上的大村落,它是聚族而居,民宅的外形,全是白墙青瓦,在村前溪光绿水的衬映下,呈现一种详和、宁静的感觉。白色在自然的空间里,不可能有纯白色的,而是变成一种乳白的复合色,特别是经过风吹雨淋后,又增添了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更令人遐想。遐想是美妙的,它让我们张开了记忆的翅膀,穿越了历史的时空,进入到那个年代……
据村中老人说,解放前,跨过桥头店的大木桥,沿溪岸的石级向东而下来到村边,村前有一座牌楼,过得牌楼,又沿石条铺成的巷道走去。巷道很宁静,径曲幽深,几曲回肠,才进入村中。村中里弄纵横,沟连巷结,形如网络,近似行宫,翘角飞檐,碧瓦泻彩,大有清溪环绕斜阳古道,桃花流水仙地洞天的韵味。还有朱门深掩,豪第栉比浮雕画坊,跃然壁上的布局,足见其物质富有与炫耀。因为这里的村民极大部份,都从事经商,不是贾儒,便是儒贾,生活非常富裕。他们是徽商的一个组成部份,也因此这里的村落建筑,都具有徽文化建筑的特色。如果你穿行在谢家村的商墙深巷的建筑群中,就有着浓厚的古色古香,仿佛进入了时间的隧道,似乎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溯到那个历史年代,又似乎进入了历史与现实交叠的虚幻境界,一种难以言状的神奇和迷惘,一种奥秘和传奇的情怀,总在你胸臆间徘徊!
此刻,站在谢家村前的平坦上,人们却在默默地寻觅着记忆中那个古韵厚重的朱漆牌楼(遗址),它标志和意味着该村的一种深厚的文化氛围,可已是不复再见了,一种失落感,让人慨然怅怅而生,……
那年,因抗战由池州迁至陵阳的池州师范,有一个这个村的名人谢光来(字涤云)老师,也在池州师范高师部任教。他是语文老师,爱古体诗词。他在1947年秋给学生讲授《屈原列传》时的一些解析和论证,其论点鲜明,考证翔实。他对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认为《招魂》、《哀郢》是宋玉所作,持反对态度,他同意太史公司马迁的考证为屈原所作。谢光来还认为写作地点是在陵阳,论证是根据《哀郢》的“今逍遥而东来”,“当陵阳之焉至兮”之句,是屈原离郢(今湖北江陵县北部)东下,来到陵阳(谢家村这一带)。谢老师此说则是根据《山带阁注楚词》卷四中的作注,在宁国池州界;又据前后汉志水经注,在宣城池州之间,地处楚东极边。再说屈原在陵阳谪居九年,也是有其诗证。《哀郢》诗中说得十分明白:“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他九年不复,而是因于那个诸候割据的战国年代,战争频仍,交通阻塞等等历史大背景的原因所形成的。屈原来到陵阳,由于战乱只能是凭借一叶孤舟沿江东下了,这不是推理想象,而是在屈原作品中有痕迹可寻,在《招魂》的尾章就有:“路贯庐江兮,左长薄。……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可见其真是孤舟一叶向东流,来到江南,来到陵阳。
这里需要对诗中的“路贯庐江”的作一点解释,庐江即是青弋江,而不是长江北岸的今之庐江县。据《汉书地理志》载,“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它确切地注释了“庐江”的航道流向。屈原在诗中也说到他的航行方向,《哀郢》中的“湛湛”、“上有枫”之句。便是指内江也即是由北向南而入泾川,泾川乃是青弋江的古称。这条江是山川,只有在进入青弋江的中游才有枫林。诗中的“左长薄”,约在桃花潭以北,左家坑以南,今之章渡镇一带。至于“上有枫”,这枫林的确切地点,那只是迷离隐约了。谢光来认为,也许就是桃花潭和漆林渡之间,乃至广阳一带……
青阳县谢家村风流探源(3)
在谢老师讲解《屈原列传》这节课之后,谢老师带学生徒步去广阳的枫树窝,寻找屈子孤舟的渡口,说起来十分遗憾,不免是无渡无舟枫也无的败兴而归。归时已午,顺路进入谢家村,那时村前的牌楼门漆尚是朱颜炫耀仍犹在,肃穆庄园气象严的古韵古味。谢老师指指门边金字对联说:这“村积陵阳水,溪流春谷泉”。联文,据说是出自谢氏远祖谢眺的手笔,也许是谢眺于公元484—490年间,在宣城任太守,曾经几度徜徉于陵阳的佳山胜水时写的。后来谢光来也撰写了一幅对联是“宝树家声看日照,玉屏山色送春来”。这副对联,至今还有许多谢家村人,过春节时年年袭用着。
“溪流春谷泉”,据说是谢家村前那条陵阳河而言,也曾是五修《谢氏宗谱》主修人谢元琦《碧溪春波》诗中的:“两岸泉飞青照眼,千层波涌碧横楼”的原型出处。从此看来,越向上古追溯,陵阳河道更是宽阔而深深。记得谢眺的《游山》诗中:“幸莅山水都,复值清冬缅。凌崖必千仞,寻溪将万转。坚愕既崚赠,回流复宛澶。杳杳云窦深,渊渊石溜浅”。此诗三至第六句,酷似琉璃岭的山形水势。后两句好象是谢家村前那条平缓而清澈渊渊的“春谷泉”。谢眺此诗,着墨不多,便将冬日的山石之崚赠,溪流之宛转,以及岫云,石濑之状态,历历展示出来,不愧是高手,是别开生面山水诗的一代宗师。
谢眺的另一首《将游山水·寻谷溪》诗也是写陵阳谢家村的灵山秀水,“寻谷溪”也许就是“春谷泉”。诗中的“既从陵阳钓,挂鳞骖赤螭……轻苹上靡靡,杂石下离离。寒草分花映,戏鲔乘空移。”这“空移”之比兴的浪漫手法和心灵妙想,妙绝了。可说是语炼意切,音节流美,如果不亲临陵阳,不会写得如此真实,也许谢眺的吟骑曾经几度徜徉在谢家村的沙堤古道上。
谢眺的山水诗是永明体的首创者,他为后来唐诗绝句又开创了新领域,是唐诗绝句的鼻祖。古诗源中有“玄晖(即谢眺)灵心秀口,有渊然冷然于笔墨之中,妙理深情于笔墨之外的评品”。谢眺之渊然深情于《寻谷溪》,几度徜徉于谢家村,我们揣想更多是他的宗兄,谢石的曾孙谢玄恺隐居陵阳(是公元454年),早谢玄晖(谢眺)20年,不知他们宗亲间可否会晤了?
继谢眺260年之后的唐代诗人李白,最为推崇谢眺,曾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的评价。李白慕屈原、谢眺之名来到陵阳一带,寻踪追迹,由青弋江(泾川)至陵阳河的南端,谢家村村南的琉璃岭(今之太平湖)。李白的《下泾县陵阳溪至涩滩》诗中“白波苦卷雪,侧石不容船。渔子与舟人,撑折万张篙。”可见其琉璃岭峡谷的水势流急和险恶。所谓“涩滩”,即是陵阳河出口的琉璃岭峡谷。“几经沧海难为水”,今日琉璃尚若然。如果有兴,不妨一行。欣赏琉璃峡谷之险隘。李白陵阳之行,是一次美妙的诗歌山水之旅,他对陵阳一带的山水人文,创作了近百首诗之多。这是天赋地灵,地灵而又人杰的美好诠注,这可说是地以人名,名随才高而形胜吧!
没错,陵阳(谢家村)这一带,曾经漂泊屈子的孤舟,徜徉过谢眺的吟骑,酣醉过李白诗魂。一千一百年间,三颗诗坛巨星相继攀升天宇,朗照在陵阳的灵山秀水间,是历史的巧合,还是造化的分外垂青?是的,不论是巧合和垂青,毕竟他们才气,薰陶了陵阳后代人的文化底蕴,同时也由于谢氏远祖的血缘代代相传,其流风遗韵,使其子子孙孙的文风都长盛不衰。就以谢氏一脉来说,儒林文苑,风流代出。
二、历史渊源底蕴深
从《谢氏宗谱》现代的以谢光来(字涤云)为主任编辑的民国壬申(1932)年版本来看,记载了青阳谢氏,源于会稽(今淅江绍兴市)东山谢氏。东山谢氏的由来,乃是领衔人物谢安出仕前长期隐居会稽东山。故后裔自称东山谢氏。远古谢氏,原本出于炎帝,汉魏以前既年代太远,又无史料可考,故称西晋谢缵为始祖。谢缵原籍阳夏(今河南太康),西晋武帝时(270—285),官居国子际酒。在整个东晋以及其后的南朝时期,谢氏族中不断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政治、军事和文学家,如政治家谢安,军事家谢玄和谢石,以及文学史上脱颖而出的山水诗的谢灵运(谢玄之孙)和颇受李白推崇的诗人谢眺(谢安之弟谢拔的曾孙)等。
青阳县谢家村风流探源(4)
陵阳谢氏之所以源于淅江会稽“东山谢氏”之由来,也是因为谢家村的始祖谢玄恺(谢眺的堂兄),乃是谢安之名将东鲁大都督谢石的曾孙。谢玄恺以明经入仕、任宣城莶判时,东晋衰败无能,政权摇摇欲坠,刘裕专权至极。谢玄恺于安帝义熙十四年(420),弃官隐遁,初隐于歙县黟山(今黄山),十年后,迁隐于陵阳丹霞山。谢玄恺的两个儿子谢麟鸿、谢雁鸿寻父亲来陵阳,玄恺将长子麟鸿留在身边,雁鸿回原籍。长子谢麟鸿于刘宋(南朝刘裕以后的文帝义隆时期)元嘉(424—454)之间,卜居于陵阳一带,开陵阳谢氏之先河。谢家村也许就在此时建立。
三、络绎人文如累叶
谢家村祖籍原于淅江会稽的“东山派系”。历史上出了不少显赫人物,虽说是属于远祖的辉煌,但也能说是陵阳谢氏的“风流”,渊源有自。笔者试图想梳理出民间流传“风流谢家村”的口碑之由来,可谱无记载,传也无据,只好集琐闻于拙作的最后章节,先说说谢家村的一些人文概况吧。
陵阳谢家村的始祖谢玄恺以及其子子孙孙,得其远祖的流风余韵,又有着九华山钟毓的滋润,文风世袭传承,文化底蕴深厚、好儒崇知,张儒求名之风,长盛不衰。
这里需要说说谢家村的经济与文化关系,也即是它的人文概况与特色。所谓特色,它儒贾并有,以贾养儒,贾是手段,儒是目的,这不单纯是其个人志趣和爱好所致,也因为个人意愿是受一定的时代制约和历史条件以及阶级关系所支配,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和时代,提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政治和文化奴役,从而“张儒”风气盛行,“儒为名高”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和世俗观念。儒学又是作为与官府往来的一种粘合剂,因为攀高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文化素养,事实也是入仕求官的通道。所以世人都在急欲“张儒”而求名,何况谢氏“名儒代有”的氏族。谢氏的“张儒”之风始于西晋时代,东晋孝武帝太元(376)时期的执政大臣谢安以前,早徽文化七百多年,而徽文化是由徽商的兴起产生的。徽商起源于南宋(1127),发展于元末明初,崛起于明代中叶。由于徽商的崛起,他们拥有丰厚的资财,一种购买金石、古玩、字画成为时尚,征歌度曲,更显高贵,形成了亦贾亦儒的世风,不少富商捐个一官半职,则是入仕的一种捷径,陵阳、谢家村也不乏其人,而谢家村不同于其它氏族的是有不少庠生以明经入仕,据其宗谱记载,摘要如下。
谢家村在他们东晋时期的远祖谢安等名人以后,由南朝及唐代,以明经入仕在朝廷(中央)任职两人,唐宗间进士三人,其中职务最高者,以明经仕梁的谢恭友,其头衔为“中书省门下侍郎”(相当于副相级),余皆普通官员或地方官吏。虽然,较其远祖谢安谢石等过去的辉煌,固然相形见绌,但也不乏世俗所称羡的朱门荣耀。此后,如明代天启(1024)时任户部太仓银库大使的谢士鲲,清代雍正(1723)时任湖南永顺府经历司经历谢昌言,乾隆(1736)时任四川布政使司经历的谢明达,光绪(1875)时任布政理问的谢振邦,都因勤谨奋勉,忠于成守,获得朝廷嘉奖并诰封其父母及祖父母殊荣。民国后期(1949)时任安徽芜湖(今芜湖市)县长谢汝昌,因坚定果断弃暗投明,迎接解放,保护了芜湖市整个区域的市容和人民产财安全,贡献卓著,获得了共产党的肯定与评价,是一位现代比较彰显而不平凡的历史人物。
由此可见,谢家村确实是儒界林立,人文络绎,其风流代出,世族繁衍,故社会知名度历来颇高“风流谢家村”之流传口碑也就传之有源了。
“风流”之传说,还有其外界客观上的一些原因,那是缘起于清代康熙末年和乾隆初期(1666—1742),谢家村有一位叫谢元琦很有才气的诗人,他同他的三哥谢元琎也是享誉很高的诗人,兄弟俩有一位京都诗友叫王文锡,因谢元琎不幸逝世,王从北京发来一首七言古风体挽诗,其中有“争颂风流”之句,也许就是“风流谢家村”的端发或出处。全诗40句,限于篇幅,只好将其首八句摘绿如下:
蓉城城南六十里,陵阳古镇名于此。相隔十里又东南,谢家旧族村蕃址。东山派系有渊源,争颂风流在村里。累叶人文络绎传。由来毓秀钟山水。
青阳县谢家村风流探源(5)
上诗的作者王文锡,是一位太史,也即是翰林,他对谢氏昆仲有所了解,当获悉谢元琎不幸逝世,表示痛惜与哀悼,发来挽词并追忆他们的真挚友谊,诗中还说了“联翩喷薄赋才华,高上词坛树霞绮”的高评仰慕之情,以及等待再次与谢元琦会晤,同时又说了“抑郁牢骚话知已”的期盼。
谢元琦在谢氏络绎人文的累叶中,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是后世子孙的敬仰者,该村现代名人谢光来老师最为追崇的这位诗人。谢光来在主修第七届民国壬申(1932)《谢氏宗谱》时,便将谢元琦的《村景题咏》七律八首放在卷首,这因其诗作不仅具有清韵幽发的特色,更为突出地展现了谢家村聚落似园林的村景的优美,绘出了一幅立体桃源胜景图的史料关系,值得遗传下代。现将其八首诗题目不妨抄下,依次为:《碧溪春波》、《沙堤柳絮》、《南圆竹韵》、《果老仙踪》、《山寺晨钟》、《东山晚霞》、《城墩红叶》、《华峰雪霁》。这八个景点各具独色,多角度、多层次、展观其旖旎风光如:
碧溪春波
览胜桃源问渡头,无边春色泻寒沤。东风乍起添新涨,北水遥连没小洲。
两岸泉飞青照眼,千层波涌碧横楼。怀才却自惭宗悫,何日乘槎破浪游。
城墩红叶
突兀高台古渡东。疏林掩映梵王官。溪光荡漾天连碧,枫叶飘摇水卷红。
山带胭脂迎细雨,枝撑玳瑁碍斜风。吾家独据桃源境,莫引渔郎入此中。
上录其诗二首,以予共赏谢家村的地灵与古往之春秋,同时也为谢光来老师考证提供屈子孤舟停泊陵阳古渡口之佐证。二诗中两处提及到古渡,也许是谢元琦与谢光来都认为屈子孤舟渡口就在谢家村南。此外,谢元琦的二诗中两处出现“桃源”,又莫不是为后来“桃花井”传说作了“桃花”演绎历史依据?
至于谢元琦的“桃源”之说,也许是诗情的虚拟?不过,沿村前溪埂由北向东南走去,经过连绵起伏的几个小山凹和几段土路,来到一处山凹,这里已杂草丛生,植被荒芜,其落寞荒丘,西风咽阵,大有湮滞寒烟伴暮鸦的况味。如说是“桃源”,毋宁说是悲凉的萧然荒漠。想当年谢元琦的“览胜桃源”,无边春色,变形了,湮灭了,眼前只剩下匝地悲鸣,低徊蛩语。二百多年后,时序交替的只是:“寂莫桃源人罕到,有谁寻觅到寒林”……
沧海桑田,人间变换,尽管谢元琦在谢氏“累叶人文”中只是一叶,可为凸显的是他给村里主修了宗谱,给后人留下了一些精神财富,这就是谢光来所追崇之所在。谢光来也同样主修第七届谢氏宗谱。在谢光来诗中曾经有这样的:“种桃夫子归何处,后继栽桃人又来。这意味了他继往开来的感慨。
四、风流有自住春音
沿单条石径去寻觅谢光来先生故居,这是心的幽唤。秋深,总觉得有点,初萧瑟瑟而风凉,忽簌簌而疏落的天气变换的感觉,秋声中真有些怅怅低回。枫叶在淡淡的斜阳折射下,显得一种红黄交织的复合色调,比起新红色来要深老得许多,似乎在人们黯淡的情感影壁上,被调了色呢?说不准,真有些“无计留春住”的感叹。也许那些墨客骚人,更有绵绵愁思幽绪呢,未必能在如今的一代人会在心灵中引起共鸣。春夏复秋冬,这是季节时序的变换,这是自然界的规律,而美好的事物,总难免随着时光的流转而消失,但在精神的世界里,美好的印象,却不受自然界规律的支配,它将长久,长久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里。这个村的谢光来和谢元琦二位都已经作古了,他们都给村里主修了《谢氏宗谱》。谢元琦写下的《村景题咏》七律八首,是由谢光来主修第七届宗谱时,保留了下来,也即是我们给他摘录在前一个章节里所见到的作品,可见其后者对前者的精神追崇。再重复地说回来,美好的印象,可以有隔世离空的神往,风流人物能够留住精神上的青春常驻,不受自然界的支配。
青阳县谢家村风流探源(6)
在我们的走访的此刻,已是“村掩胭脂迎夕照,西边霞色染黄昏”的黄昏。这夕照晖映,正是直射在村中,这增加了这处庭院的开合隐露之美,些些院落墙头的零落枝头,虽有隐约胭红,却已失去了当年桃李盛开的风华极态。而那桃花开出一片绯红色的云彩,不是今天来不逢时,确切地说已不复再见。眼见到的一些庭院门坊,那多种造型的古色古香,也已剥落得稀疏和残缺不全了,但古韵尚可值得去寻味,这些传统文化的国粹,却让炎黄的子孙们能可去领略它的真谛。当我们踏上一段石板的巷道时,那石板之下,似有细水流声,仔细听来,如歌行板,遥想当年那碧水萦流,穿村绕户,那该又是一番:恰似那盈盈流盼兮门前水,流不断绿水悠悠的谢家村独特韵味啊。
踏着被岁月磨光断断续续的石级走出巷道口,蓦然回首,那淡淡的胭红夕照余晖,它蕴含着一种历史的呼唤,那是当年谢光来老师在《执教》诗中的行呤:“多少年来执教鞭,耕耘辛苦亦欣然。甘将浅识凝成雨,润物功成心也甜”。这个时期,他已近暮年了,他执教孜孜不倦的精神,可说是:“渐残蜡烛熖犹红”来形容他。他执教为什么如此之执着呢?用他自己的话说:“诲人事业最堪称,如烛焚身应诺承……”他立身入世,有过一定人生的信念与追求,族长们也寄与了他很大的希望,他都能够去履行自己承诺,他为村里主修了第七届(民国壬公元1932年)《谢氏宗谱》,可说是“争颂风流在村里”,获得了族长们的认可和好评。至于功名欲望,他不是没有光宗耀祖的思想,从他的“笔劲参差未放声,凌云难直志难成”来说,也许有由于远祖谢玄恺遁迹类似难言之隐。而他身处军阀混战的年代,又“故士难离骨肉亲”的关系,他从徘徊与徬徨中走出来,走向属于自己的海洋中去—教书!
从此,他迈上讲坛,迈出了命运性的一步,选定“绿叶”事业!他将如绿叶一样,默默地给红花输送活力和营养,迎来满园春色。
他从谢家村走过沙埂上通往池州师范,只需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久久就变得漫长、漫长……在那条沙堤走得沙沙作响的小路上,曾经投来惋惜的目光,他穿越过那目光走过去,他有过悲哀,也有过再度徬徨,但他还是拨开世俗的哀叹走过去了。
记得他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没有伏羲氏教人狩猎,没有神农氏教人稼穑,人类能摆脱愚昧成为造物主的宠儿吗?如果没有至圣先师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导弟子,人类能造就文明成为自然界的骄子吗?
到课堂去,天天去,一生都去,他用热情燃亮出自己智慧的烛光,照亮着学生,朝朝暮暮在他耕耘的土地上,将成长出不止一个象他一样的教师,不止一个象他一样的诗人和文学家……学生们在各自理想的海洋上将比自己游得更好、更远。他们在成长岁月的进程中,一个个频频回首,以笑脸向自己的老师注目、凝视,他醉了!是的,“翰墨醇香更醉人”!
水碧枫红夕照妍,谢家村里绕暮烟,时过黄昏,山岚烟拥,我们该是回去的时候了。当我们来到谢光来老师故宅前,伫立很久,很久,又想留点什么以作告别,于是,这样的诗句便涌出心田:“故宅园庭难复修,凄凉频起上眉头。师恩诲益人何在,凭借诗声祭墓丘”。
庭前吹来一阵秋凉的西风,带来了飘落的枫叶,它以历史的徐旋在诉诸我们,谢光来先生执教的决择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是永恒的,让人铭记在心。
谢家村,我们从你的深处见到了你“风流”的底细,了解到你延续千百年来的“风流余韵”。谢光来老师的风采,鲜明地展示了他绵绵不尽诗韵的潜流,他“桃李连天下”的人生业绩,则就是桃花之魂,风流之魂!!
谢家村美好的印象,这样的一副对联可以作结:此地经过春情驻,伊人宛在梦云间。
本文已近尾声,忽然想起来青阳一带流传的口碑,“风流谢家村”久有“桃花井”之传说,说女人喝了井中水,就能变得丰姿绰约,仪态万方,苗条楚楚,风情万种……
就这传说,谢氏宗谱从无记载、从无定论。谢光来先生生前曾风趣地说过:“一个历史的胜地,就会演绎或杜撰出一些神奇的故事来,我们从不计较这个附会的传说,讹传是处又何妨”呢?
桃花井传说的只言片语,要说是无中生有,也未必尽然。上文中提及到谢元琦的《碧溪春波》、《城墩红叶》中就有“览胜桃源问渡头”和“吾家独据桃源境”之句。也许就由此演绎而来,如果真是其出处,那就不是空穴来风,而只是一种对谢家村的美化,微妙地对其自然生态,人文环境的山美、水美、人也美的扬名,这又何不好呢?没错,这就是“讹传是处又何妨”真正的内涵和底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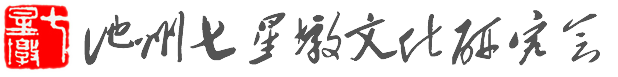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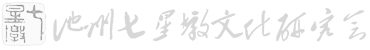
 皖ICP备14013909号
皖ICP备14013909号